“柏林病人”的成功是个无法复制的奇迹
未来5年,英国科学家将继续在这一突破性治疗领域进行钻研。即使在最绝望的时刻,“柏林病人”的存在也始终意味着一丝曙光。毕竟,面对医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人类也曾误打误撞地取得胜利。
在“鸡尾酒疗法”问世前,艾滋病病毒始终是个令人闻之色变又束手无策的恐怖杀手,沉默地收割着数百万条生命。1995年,这种联合使用几种抗病毒药物的高效疗法,为黑暗的隧洞里蜗行摸索的人类点燃了第一支火把。
迄今为止,“鸡尾酒疗法”已经帮助1000多万艾滋患者稳定病情,但它价格昂贵,要求坚持定时定量服药,还会对病人的肝肾产生难以承受的负担,在医疗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明显效果较差,且无法彻底根治艾滋病。
直到一只脚差点踏进坟墓的布朗恢复健康,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了第一例被治愈的艾滋病例。
起初被建议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时,布朗对这一方案拒不接受,他不愿意冒着死亡的危险去做一只小白鼠。柏林查理特医院的格罗·胡特尔医生也承认,病人当时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5%。但在步步紧逼的癌细胞面前,他不得不妥协。
那是在2006年,接受艾滋病治疗十几年后,布朗一次骑自行车时突然感到极端疲惫,送到医院后被诊断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接连三次化疗失败,严重的并发症几乎让他命悬一线。
考虑到患者原有的病情,胡特尔医生从60多位候选人中,精心选择了一位非常特殊的捐赠者——一个天然对HIV病毒免疫的男孩。
由于CCR5基因编码区缺失,他无法合成CCR5细胞膜蛋白,而缺了这个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HIV病毒根本无法攻城略地、入侵细胞。这种起源于中世纪的基因突变,可能是在应对鼠疫或天花的过程中产生,只有约1%的北欧人从祖辈身上继承了这种珍贵的“免疫基因”。
2007年和2008年,布朗接受了两次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比所有人预期得都要成功。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停止鸡尾酒疗法治疗3个月后,血液检测表明他体内的HIV病毒已经彻底消失。到2007年年底,他已经能够和常人无异地回到办公室和健身房,艾滋病病毒至今仍未“卷土重来”。
“在这个大家甚至不敢大声提到‘治愈’二字的领域里,这绝对是个振聋发聩的发现”。当布朗宣布被治愈时,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
研究人员指出,有三种不同的因素的单独或共同作用,可能使布朗摆脱HIV病毒。一是在骨髓移植准备过程中的X光检查和化疗摧毁了他的免疫系统,进而杀死了沉眠其中的HIV病毒。二是发生了移植物抗宿主病,新免疫系统对原有的T淋巴细胞发起了攻击。第三种可能,则是骨髓干细胞供体身上有罕见的基因突变。
发生在“柏林病人”身上的奇迹,仿佛给全球医学界打了一针兴奋剂。科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争相踏上了这条隐约通往终点的道路。
2013年7月,两名同时患有癌症和艾滋病的“波士顿病人”接受骨髓移植治疗,在停止服用ART药物后没有在血液中检测到HIV病毒,医生判断他们的艾滋病可能被治愈了。但仅仅到6个月后,病毒就开始大规模反扑。
同一年,被称为“二号病人”的明尼苏达州男婴,接受了当初为布朗捐献骨髓的供体移植,试图以同样的方式重现布朗的奇迹。但次年7月,科学家发现男孩血液中HIV病毒显著增加。
美国埃默里大学免疫学家圭多·西尔维斯特带领的团队,则致力于研究辐照对消除HIV感染细胞造成的影响。他们将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感染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的恒河猴体内,并使其暴露于高剂量的辐射中。但试验结束后,猕猴体内的病毒数量很快迅速反弹。
当初轰轰烈烈开展的实验一个个黯然收场,科学家终于无奈地意识到,无论是否存在成功的可能性,骨髓干细胞移植都不会成为人类探索艾滋病治疗的最终答案。这种手术实施难度大,潜在的危险性很高,寻找匹配的供体更是无异于大海捞针。正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保罗·沃尔伯丁所说,“柏林病人”的奇迹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它不是个可以广泛借鉴的病例。
这个结论让布朗感到难过。尽管体内的HIV病毒已“一去不返”,但他始终将自己当做艾滋病群体中的一员,“不会有任何其他身份”。他深知自己的幸运,但抛弃同伴独善其身的愧疚感,多年来始终蚕食着他的内心,“我不想成为唯一被治愈的艾滋病病人”。

 大成资讯网微信
大成资讯网微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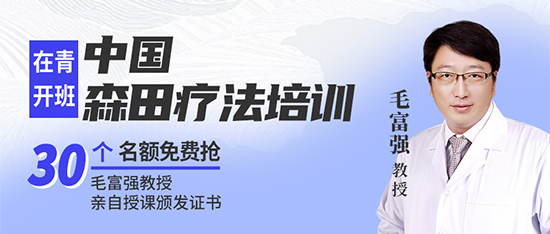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