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斌被调离县城,莫名罢去副院长职务,到二十公里外的脉地公社医院做乡村医生。
脉地是个山区小镇,从这里翻过两座大山,跨越多条沟涧,才能到达海拔2578米的莲花山麻风病院。麻风病院有一百多病号,收治邻近几个县的麻风病人,医生已下山闹革命,山上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两个赶马帮运输物资,一个负责发药管行政。
樊斌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查出患麻风病后,回去就上吊死了。麻风病是个非常恐怖的社会问题,得了病就像被判了死刑,遭到家庭和社会的抛弃。联想到自己,打成右派,发配边远的异乡,如同“政治麻风”,樊斌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和感慨。
他开始钻研麻风病学,研究麻风病病理,以及麻风病的社会问题。1969年,樊斌提出申请,自愿到莲花山麻风病院当医生,他要去与世隔绝,被遗忘的大山的皱折里,和一群被开除“人籍”的手蜷足跛、鼻塌眼斜的残损的生灵生活在一起,医治他们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用深切的同情、宽厚的理解这种人性的光辉,去烛照生命遂道中最黑暗的一段。
从北京的莲花池,到西南大山里的莲花山,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樊斌似乎与莲花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莲花山麻风病院,当上了医院唯一的医生,樊斌经常是一个人守一个医院,一个人守一座山,过上了“世外桃园”与世隔绝的生活。
首先面临的是,麻风病人抵触情绪太重,不太配合治疗,认为治与不治一个样,即便治愈出院,也很难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很难得到家人和社会的接纳。有的病人甚至怨恨医生诊断出病来;有的病愈了,追着医生要求“平反”、摘掉“麻风帽子”。有两个人病愈回家,不仅家门紧闭,还放出狗来追咬,一个吊死在门口树上,一个撞死在自家门前。有的人治好了病也不出院,要求继续在麻风病院呆下去……面对这样的社会压力,樊斌感到震惊,决心从根本上帮助他们。
樊斌知道,现代医学已经打破了麻风病不能治愈的偏见,并用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证明了初期患者的治愈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但可怕的是麻风病人就隐藏在民间,成为最危险的传染源,所以,消除偏见,减轻患者的精神负担,让初期患者得到及时治疗,才是有效医治麻风病的关键所在。“保密治疗”——一个大胆的构想让他激动不已,他印制了大量的宣传传单,在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种会议上散发,宣传相关知识,让病人和健康人群了解到,麻风病并不可怕,而且能够治愈,同时,告诉病人主动和医生“单线联系、秘密接触、领药回家、定期检查”的“保密疗法”。
那时,樊斌经常下山,而且显得特别繁忙,一到赶集天,他家门外墙脚树下,常常蹲有奇奇怪怪的人,他总会第一时间发现病人,为他们检查,给他们发药治疗,实施独创的“保密疗法”。 麻风病人不用再住院治疗,不用再与世隔离,甚至没人知晓就被治愈,这种独特的治疗方式,简直成为麻风病人及家属的福音。
一段时间后,樊斌不仅被病人接纳,还被病人和家属视为菩萨,供奉进绝望空寂的心灵殿堂。
在身体健全人的社会里,樊斌是个被抛弃的角色,在那些充满绝望无助和痛苦的非正常人眼里,却又是个受人尊敬爱戴的人。他敢吃麻风病人的饭,敢喝麻风病人家的茶,他的病人,以虔诚的目光追踪着他,以面佛的心情信赖着他,以顶礼的方式迎接着他。
在不公平的阴影里顽强地奋斗,收获公平;在绝望的土地上坚韧地劳作,播种希望,这是樊斌用生命写就的一部浓缩的巨著。
1986年,樊斌离休了,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他每天读书看报,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党的每一次重大改革。《城》继续在他的笔尖跳动,采用短篇小说或散文等不同的文学形式,一点一滴再现他的梦想。在他的生命里,《城》是他的孩子,是他的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城》使他的生命辉煌,也让他跌入万丈深渊。樊斌无暇后悔,也不屑怨恨,不争不求使他心平气静,他感谢上苍给予他最宝贵的生命,生活给予他最难得的经历,他由衷地感谢生命,感谢生活。
2012年10月27日,樊斌像往常一样,倍老伴去买菜散步,回来途中,他感觉到心脏异样,急急走进干部干休所大门,一个踉跄,他倒下了,笔直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无声无息,安详恬静......
一个月前,樊斌刚刚度过86岁生日,孩子们开玩笑说:“老爸能活一百岁”,他摇摇手,笑咪咪地说: “够了,够本了!”

 大成资讯网微信
大成资讯网微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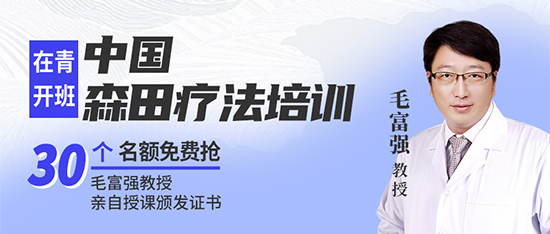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