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医学人类学学科概述:
医学人类学是利用人类学的理论,从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个视角,研究健康、疾病、治疗等社会现象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起源于对于非西方民族田野调查的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医学人类学发展成一门重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以哈佛人类学教授克莱曼(Arthur Kleinman)为代表人物,强调文化在治疗中的重要性,丰富了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的内涵。198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出版的《医学人类学论文文集》,标志着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正式进入我国学界的研究视野[5]。
改革开放后,医学人类学在国内发展迅速,其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可分为体质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两大方向。体质生物性方向的医学人类学,主要研究多民族体质特征和遗传多样性。社会文化性方向的医学人类学包括民族医疗文化、传统医疗民族志与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医患关系问题也属于该领域,然而,国内相关学者单独针对医患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多见。
三、医学人类学对医患关系的解读:
1. 整体观的研究取向
整体观是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论,指的是系统是作为整体起作用的,因此系统的单个功能不能通过单个的部分去理解。同时,整体观也是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指的是任一文化要素都应该放置在整个文化网络之中去理解。因此,医患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正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缩影,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历程中,不同社群文化知识体系碰撞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医患关系问题,应借助人类学的视角,特别是整体观的视角,放到中国整个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去分析。
2.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的区别
克莱曼对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区分,疾病是生物学或生物化学意义上的功能失调,是西方现代医学的概念;病痛是特定文化脉络中患者对于身体不适的认知,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着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6]。疾病和病痛都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特殊布局中的构建物,必须在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环境中理解和领悟其蕴含的丰富意义。
两者不一定同步和对应,在现代临床医学实践中两者有可能表现为对立。据统计,约50%寻求诊疗的患者在病理学上查不到异常[7],疾病也可能不伴随有病痛的感受,相同程度、相同病理的患者描述出不同程度的病痛和焦灼感[8]。而这种病与痛的背离,往往成为医患矛盾的源头。当医生通过使用各种先进的诊疗手段使患者病情好转,然而此时患者并没有出现病痛的减轻,便责怪医生医术的无能。
关于病痛(illness)的概念,狭义而言,它是患者的肉体感受,广义而言,它是指患者在疾病的刺激下,在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认知反应(包括对于病情严重程度的自我判断,病情治疗效果的评估)和策略行为选择(是否选择就医,选择怎样的医疗模式,什么时候停止治疗,医疗价值的评估)。患者对于病情和诊治效果的评估是多元且动态的。在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知识、社会等级背景下,患者的病痛感受不同。医患双方对于疾病与病痛的不同认知,是医患分歧的源头。

 大成资讯网微信
大成资讯网微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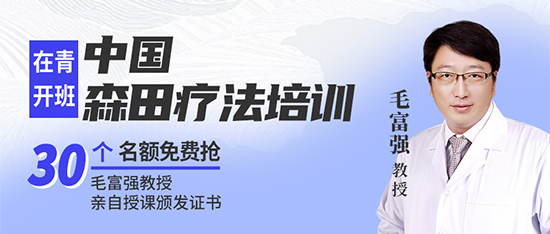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