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疾病的文化建构
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疾病是一种生理的事实,是唯物的现象,是人类身体在生物性和化学因素作用下异常变化的描述语言,但却忽视了疾病是文化建构的概念。医者这种预设的立场会导致实践与认知的误区。
其一,重视实验证据,强调身体的物质性的生物医学,其哲学基础是强调身心二元分离的科学主义,将病患的身体客观化,因而医者容易忽视了患者的个体独特性,患者心理、文化、社会因素的差异。在诊疗过程中,医者“医病不医人”,治疗了患者的病症却可能无法恢复其受损的社会功能,未根据患者文化特性而制定的治疗方案可能因患者的排斥而效果不佳。
其二,在当下全球医方卫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主流生物医学知识体系,只是平等的民族医学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一套知识与象征体系。医者忽视的是,他们关于疾病的解释是以现代生物医学知识为根据,运用了多种指标与象征体系,并非是全然客观的事实阐述。
因此,从疾病的名称和概念可以看出其历史的建构,以“战后心理压力障碍”为例,是越战退伍军人与卫生行政人员为了使其心理创伤具象化,使第三方在支付保险时有据可凭而建构的病种。
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不同民族,为了适应不同的情景,对于疾病概念有着自身独特界定的认知和实践活动,这一整套的认知与实践共同构成了有关疾病的概念文化体系,如中国的藏医、苗医等少数民族医学,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a)医学等。疾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什么样的征兆是疾病或是日常的生理反应,疾病程度轻重如何界定,什么病必须是禁忌的和不耻的,而什么病是日常普遍的,都包涵在这套疾病的知识体系之中。
再者,疾病概念变化反映了对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的“适应”。根据克莱曼在中国湖南的研究显示[9-10],20世纪 60年代“神经衰弱”这一在西方已被精神病学家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删除的病症,却在湖南各医疗机构门诊诊断中普遍存在。其原因在于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1)相对精神病这样被污名化的疾病,神经衰弱是一个中国文化体系中更容易被接受的病种, 更可获得社会认同。(2)多数抑郁症患者在“文革”中有着不幸的遭遇,“神经衰弱”的诊断也是其在强大政治权力之下的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途径。克莱曼认为这是“社会问题躯干化”,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社会出了问题, 结果社会用“神经衰弱”这个病种做了代替品。

 大成资讯网微信
大成资讯网微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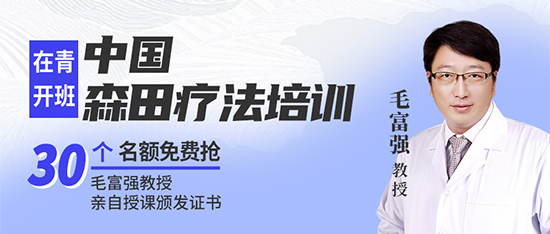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