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医者与患者的不同解释模式
克莱曼[11]将医患双方对于疾病的认知,概念化为“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s)。最初克莱曼为了区别疾病和病痛,而借“解释模式”的概念,强调医患双方对于疾病认知的不同,所谓医学概念也是植根于文化和历史语境之中的“解释模式”。
医者对于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先进的医疗检查手段所显示的精确的数据与图像,其判断背后支撑的逻辑是基于生物化学的知识和技术与过往诊疗经验的总结;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是建立在个体切身感受,因其缺乏专业严密的医学知识,其主观的直觉式的判断更多地是建立在个体体验与经验、求医经历、民族文化体系、社会舆论的引导、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方面[12]。中国医生大都有着相似的五年以上正规医学教育背景,然而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却多元而广泛,因此,患者对病痛的认知也呈现多元多样的层次。
王路等[12]的“医患关系的认知人类学解读——基于广州儿童医院的调查事例”中所提供的吴康个案中,患者的父母都以为孩子患的是“猪毛虰”地方性疾病,在其地方社会经验中这是较容易治愈的“小病”,而无法接受医生诊断为“脑炎”,并且有生命危险的事实。而吴康的医生则认为,很多医学上的病在地方有其他称谓,然而这些称谓却没有医学上的参考价值。
由此例可看出,在医患双方互动的过程中,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猪毛虰”与医者的诊断“脑炎”发生碰撞,其实质为双方对同一疾病“解释模式”的不同,根本在于双方文化知识体系背景的不同,民间经验与专业医学知识碰撞。医患沟通的矛盾便在于,医患双方是在用不同的语言沟通,医者多用精准的医学术语,而患者更多的是在使用民间经验描述病情,如此,患者无法理解医者的解释,而医者认为患者对于病情的推测,即患者的解释模式,没有价值,于是便站到了话语权威的位置上。医患双方若要达到良好的沟通,需要的是彼此解释模式的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
20世纪70年代末,克莱曼[11]针对医患双方解释模式的矛盾,曾倡议发展临床社会学,在医学院和医疗单位增加社会学视野培训和课程,使医护人员具有社会学的涵养,在医疗实践中更好地理解、服务患者。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出台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体现了由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内在医学院开设医疗人类学以及相关临床社会学呼声也越来越高[13]。
当前国内医患矛盾突出,医疗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医疗保障体制性问题等客观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改善医患沟通成了缓解医患矛盾的可行之策。加强医护人员的职业素养,培养医护人员广阔的临床社会学视野,是解决医患沟通问题和制定科学的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条件和正确出发点。

 大成资讯网微信
大成资讯网微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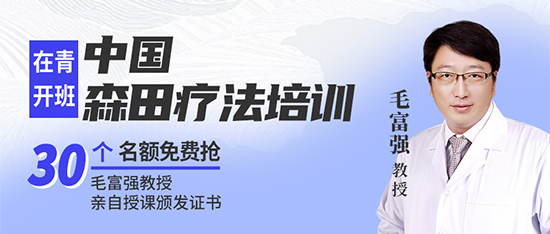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
鲁公网安备 37020302370486号